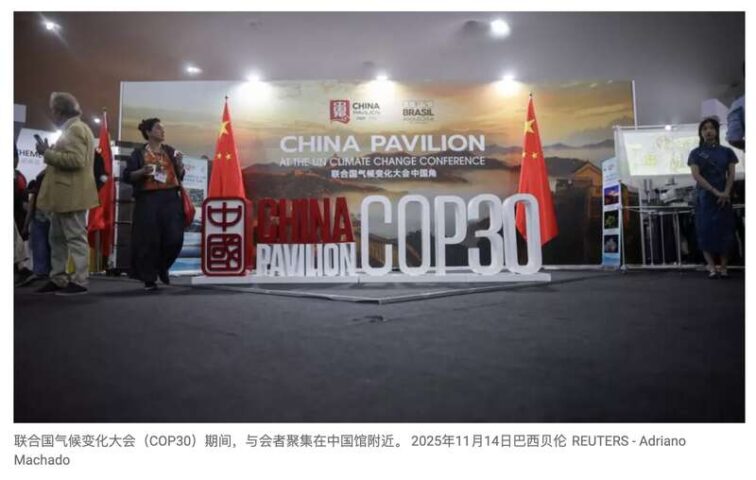内容提要:
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将中国科创处境形容为“悲壮”,指出面临僵化和低效、认同缺失、科研追求误区、教育断层及国际围堵五大障碍。强调科技创新是中国唯一希望,必须打破理念体制束缚,推动教育革命与自立自强,在大国博弈中实现从0到1突破。

近日,曾提出“无科创、无未来”主张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,在10月23日纪念复旦管院恢复建院40周年的“国际商科教育博览会”媒体发布会上指出,面对与美国激烈的科技博弈,中国正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,但目前中国社会对于在科创时代,什么是最核心、最稀缺的要素,认识却远远不够。
而对于中国当前科技创新的处境,他直言面对理念和体制束缚、教育断层,以及多方围堵等多重挑战。中国的科技攻坚,迈向科创高地,“就像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一样悲壮”。
他在发布会后在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记者采访时解释说,“科创是中国唯一的希望,也是中国本世纪与全球其他国家同台竞争的唯一入场券”。“悲壮”这个词不仅“充满了强烈的紧迫感”,还是一种忧患意识。
总结其谈话,能够看到他对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五大障碍的心急如焚的担忧。
一是僵化和低效。

中国科研与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国有科研院所、大学和企业,与西方以民间资本驱动的灵活体制形成鲜明对比。陆雄文指出,我国官本位传统在国有机构根深蒂固,导致体制僵化、决策低效。宝贵科研资源往往陷入行政审批与层层汇报,无法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。相比之下,美国等国家通过市场化机制,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的高效转化。中国虽有大量研发投入,但转化率较低,部分项目因官僚主义而延误时机。这种“相对僵化和低效”的体制,已成为制约“从0到1”原创突破的瓶颈。只有深化改革,引入更多市场活力与民营力量,方能激活创新潜能。
二是认同感缺失。

尽管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口号已提出30余年,但中国社会对“科创要素至上”的认同仍未全面确立。许多人仍视资本运作、商业模式为更“安全可靠”的路径,而非高风险的硬核科创。这种理念滞后,导致资金与人才偏向短期回报领域,科创企业融资难、估值低。社会崇尚“快钱”文化,忽略科创的长周期与不确定性。比如美国排名前十的科技公司,挣了钱都在投入科技创新,我们几大闻名遐迩的科技公司,挣了钱都在放高利贷。
在中美科技博弈加剧背景下,这种认同缺失让科创启航“格外沉重”。唯有全社会形成共识,将科创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,方能汇聚资源,推动自立自强。
三是科研人员的追求误入歧途。

大量科研人员陷入“论文、职称、奖项”的追逐,宝贵资源耗费在申报评审与形式主义中。这种体制难以孕育真正颠覆性创新,“从0到1”的原创突破被评估指标绑架。许多科学家为帽子、项目经费疲于奔命,忽略基础研究与市场应用。相比西方科学家专注好奇心驱动,我国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,导致浮躁风气盛行。
所以我们看到了,所有原创性的科学技术,皆出自欧美。日本人口规模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,却已经获得28个诺贝尔科学奖,而我们最近几年沉醉于论文世界第一、专利世界第一,除了屠呦呦之外,一直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。
如何改革对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,鼓励失败容忍与长期投入,让科研人员回归科学本质,至关重要。只有解放生产力,方能涌现出诺贝尔级成果。
四是教育断层。

上图为外国的小学教室。

上图为中国的小学教室。大家可以比较这两张照片,看看中外教育的区别在哪。
陆雄文称,中国顶尖科创企业核心技术人员超八成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,这暴露本土教育体系的深刻断层。他在调研中发现,高中应试教育“榨干”学生潜力,导致大学阶段丧失好奇心与原始动力。学生从“被动学习”转向“躺平”,服从思想过剩,却缺乏批判思维与动手能力。根源在于教育改革滞后,忽略个性培养与创新启蒙。不开启深刻改革,科创“源头活水”将枯竭。
陆雄文强调,教育是科创根本,必须从基础教育入手,恢复求知热情,培养敢于质疑、勇于探索的人才,方能支撑科技自立自强。
五是价值观的对立导致中国的科技创新成为被多方围追堵截的“超级战场”。

陆雄文认为,价值观的对立导致中国创业者一登场,面对的就是一个充满国际化竞争、被多方围追堵截的“超级战场”。这导致科创企业的供应链布局、技术的引进与合作,都可能因大国政治博弈而面临巨大不确定性。“我们今天的科创企业不仅要参与竞争,还要在一条充满人为设障的赛道上争夺未来,难度之大可想而知。”
面对技术封锁,一方面我们在对外交往中、在社会制度中不应将中西体制、中西文化划分得过于楚河汉界,避免一切不必要得价值观冲突,化解西方在培养人才、科技交流方面得戒备之心。另一方面,中国科创企业也不要抱有幻想,必须将技术自立自强作为根本出路。这意味着要持续投入研发,敢于在关键领域实现国产替代,最终迈向前沿原创技术的突破。
总而言之,这场科技创新的“超级战场”虽艰难,却是中国迈向科创高地的必经之路,唯有悲壮前行,方能赢得未来。